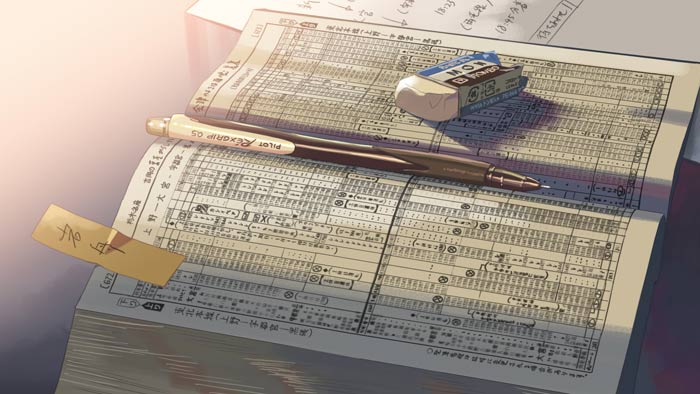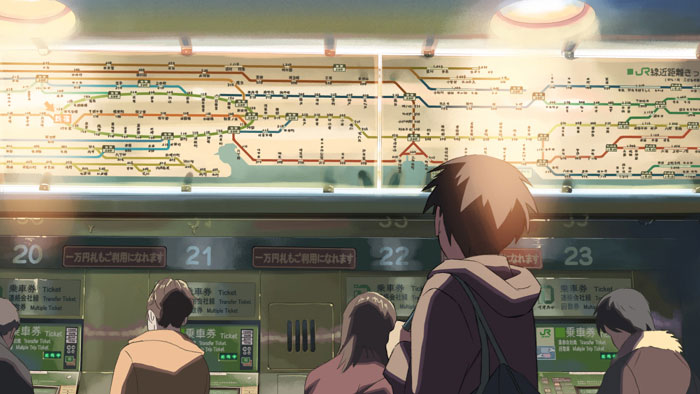中大校友關注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題目安得非常貼題,妙絕。
還未“入手”(注)只得看帶來日本的龍應台文章,也是高興。
引用一些在這裡:
====================
將燈泡黏到牆上
有沒有國際觀,能不能與國際接軌,不在於英語說得流利不流利,而在於有沒有深刻健全的「全球公民意識」;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學英語,就有了國際化,有了全球視野嗎?
一個來自沒水沒電的山溝溝裏的人第一次進城,很驚訝看見水龍頭一扭,就有水流了出來。很驚訝看見牆上的燈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一節水龍頭和一個電燈泡。回到家裏,將燈泡黏到牆上,將龍頭綁在棍上。結果燈不亮,水也不來。一個北方荒地的人走過南方沃土,看見一片葱綠豐美的樹林。他把樹全砍下,把樹幹像棍子一樣一根一根栽進他的荒地裏。等了一年,沒有樹林,只有棍子。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樹幹何以成林?因為樹幹下面緊連着一套環環相扣的生態鏈結。語言何以啟蒙?因為語言後面有着一整套幽微細緻、深奧繁複的思想系統。我們知道沒有後面那個無形的網絡鏈結,燈泡不發光、龍頭不出水、樹幹不抽芽,但是請問,為什麼我們認為英語會帶來全球視野和國際觀?
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裏,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
引自龍應台“為什麼燈泡不亮 ———我看香港的「國際化」”
==============================
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引自龍應台“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
====================================
短評:
要評論香港以至其他洋奴心態,可用
貼錯燈泡拜錯神歸結。
====================================
發揮:
觀看本地某些(只是某些,嘿嘿,不是說你)評論日本的心態
一方面不知道日本發生什麽事,
一方面又無意識地引用日本的東西來講HK,
兩面不討好,如同傻子。
譬如報紙的什麽日本明星新聞,
像拿個日本牌位做錯儀式拜錯神;
又如報道評論裏面,
人講什麽我講什麽像貼錯燈泡,
以爲能解決“同樣的”社會問題。
離棄語境去思考問題,危機一發,
特地引用於此自我警惕。====================================
註解:
為響應國際化,
我提議大家來學學當年清末民初留日的知識分子,
來一個第二次日化漢語運動----
特此聲明:
讀歷史知道知道連“浪漫”“經濟”“社會”等大量常用中文詞語,
原來是日本人翻譯的,爲免雙重標準。
本Blog宣佈以後這裡一律使用“元氣”“入手”“格好”等詞語
均為合法,但不保證去答公開試的時候不會扣分(笑)